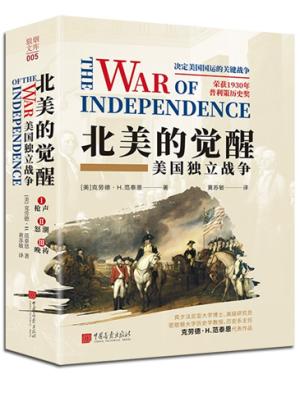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日军的“治安战” 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
》
售價:HK$
79.2

《
了不起的她,写给所有不甘平凡的女性的生命蜕变指南。
》
售價:HK$
86.9

《
皮肤的救赎
》
售價:HK$
96.8

《
六世同堂:美国百年代际变迁(1925—2025)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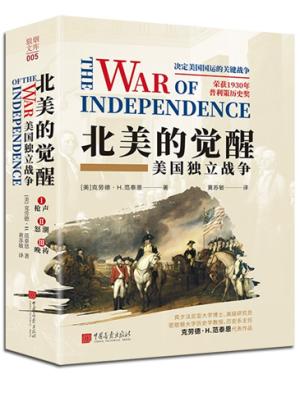
《
北美的觉醒:美国独立战争(全3册)
》
售價:HK$
173.8

《
遥远的不莱梅(直木奖获奖作家重松清超人气暖心疗愈系小说!)
》
售價:HK$
54.8

《
名士的反抗:从孔融到嵇康
》
售價:HK$
96.8

《
万千心理·图式疗法临床实践:模式工作模型应用指南(原著第二版)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
本书是关于艺术和人类学两个学之间互相倾慕、互为榜样,借鉴彼此的理论与方法,共同面对问题与挑战,携手走向未来的故事。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收录了17篇西方人类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共分为三个部分:(1)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现状与反思(第一至六篇),此部分主要从艺术领域与人类学合作的语境中探究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的当代挑战和现实机遇,指出传统人类学在学科和方法论上面临的困难,与艺术能为人类学提供的新思路和新方法;(2)人类学与艺术学的关键概念与方法(第七至十二篇),此部分主要阐释人类学与艺术领域在合作中涉及到的一些关键概念和基本方法,如挪用、场域、访谈等;(3)民族志方法的艺术成果(第十三至十七篇),这一部分主要展现在人类学方法的加持下,艺术领域在策展和影像民族志方面进行的实践。
|
| 關於作者: |
|
李牧,1984年2月生,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民俗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当代艺术与人类学、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著《遗产的旅行:中国非遗的北美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获2023江苏文艺大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2023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入围奖,译著《视觉艺术的现象学》入选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3项。
|
| 目錄:
|
序言
第一部分 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现状与反思
费尔南多·卡萨迪利亚,乔治·E.马库斯
田野中的艺术家:在艺术和人类学之间
乔治·E.马库斯
艺术与人类学中的当代田野调查美学:合作与介入实验
乔治·E.马库斯
在人类学数十年的变革中指导研究生研究的民族志回忆录笔记
乔治·E.马库斯
类同:当今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和艺术作品中的民族志
阿恩德·施耐德
艺术与人类学之间:当代民族志实践
安娜·格里姆肖,阿曼达·拉维茨
民族志转向与展望:艺术与人类学重组之批判路径
第二部分 人类学与艺术学的关键概念与方法
杰拉尔德·L.波丘斯
回归技术:民俗艺术的诠释维度
詹姆斯·克利福德
关于收藏艺术和文化
权美媛
一个又一个地方:对场域特定性的说明
阿恩德·施耐德
论“挪用”:概念的批判性重估及其在全球艺术实践中的应用
阿恩德·施耐德
作为实践的挪用·导论
稻垣立男
作为艺术实践的田野调查
第三部分 民族志方法的艺术成果
阿恩德·施耐德
艺术与民族志实验的三种模式
克里斯托弗·赖特
身临其境:关于观察和情境的说明
阿恩德·施耐德
异见与共识:与阿根廷科连特斯艺术家的田野合作
海蒂·盖斯马
人类学的艺术:论民族志展示中的当代艺术
罗杰·桑西
《作为策展人的人类学家》导论:镜中的人类学与策展
后记
|
| 內容試閱:
|
序言
艺术人类学是人类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互结合而构成的交叉学科,它既可以被视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子类,亦可被归入艺术学理论的下属范畴。其基本的研究理路是以艺术作品、艺术家和艺术事件为主要的关注对象,通过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认识和理解艺术以及与特定的艺术对象相关联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从而达到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状态、社会的互动机制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探讨和有效阐释。
一、 艺术人类学的早期历史与民族志取向
艺术人类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历史,始于20世纪初期的欧美学界;但是,人类学与艺术学之间的结合,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世界便已出现。不过,现代人类学直至1871年才正式出现(以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二者最初的结合形式主要表现为艺术家对于异文化资源在具体创作实践中的利用(这一模式一直持续至今)。例如,威廉·鲍威尔·弗里斯(William Powell Frith)便大量运用当时人种学(体质人类学之前身)中的颅相学(phrenology)知识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种族进行描绘,通过画面表现个体外在相貌与其社会身份高低和道德形象好坏之间的“联系”。然而,随着人类学学科的知识积累和范式转换,维多利亚时代关于种族与阶级的人种学观念很快遭到了来自艺术世界的质疑和挑战。作为巴黎人类学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Paris)的会员,雕塑家查尔斯·科迪埃(Charles Cordier)秉持种族平等与文化多元的态度,认为各民族不应遵循同一的“美”的原则。他的作品旨在呈现各民族体貌特征上具有差异性的“美”,通过艺术创作反抗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优劣观念。科迪埃被认为是法国第一位创作民族志雕塑(ethnographic sculptures)的艺术家,与弗里斯不同,他的创作灵感并非来自间接的文本知识,而是源于自身与其他非西方种族(如阿拉伯人、黑人及华人等)的日常交往和深入调查。可见,弗里斯与科迪埃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二者获取关于“他者”知识的路径差异:前者主要来自间接经验(文献资料),而后者则主要来自直接考察(田野调查)。艺术史家格罗塞1893年首次出版的《艺术的起源》一书,便可视为具有人类学倾向的艺术理论著作,其研究资料的来源与弗里斯相似,主要依靠文献资料。
然而,科迪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即田野调查方法,或者,从更为全面的意义上而言,民族志方法(包含田野调查和调查后的文本写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也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相关学科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它起源于欧洲殖民者对非西方地区,特别是最终成为其殖民地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地的殖民活动中进行的文化记录。在美国建国以后,出于对本国境内印第安人管理和控制的需要,美国学界对民族志方法推崇备至,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便是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博厄斯于1927年出版的《原始艺术》(Primitive Art)一书,或可视为艺术人类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真正确立的开端。从此,田野调查(直接民族志经验)成为人类学进行艺术研究时收集资料最为重要的路径和方法,它的广泛运用使得早期人类学研究从文本取向转变为语境取向。
基于艺术与人类学早期交汇的事实,可以发现艺术人类学指涉的两个视角,一是人类学本位的视角(对于社会生活全方位的研究视角),将艺术看作理解特定族群(特别是那些处于政治、经济、文化边缘的族群)的文化整体(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象征系统的媒介;二是艺术学本位的视角,将人类学方法视为进行艺术活动和艺术事件分析的手段和工具。从人类学本位的角度而言,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关注的重点在于从整体性视角考察艺术在社会中的功能,特别是规模较小的非西方社会,极少关注个体艺术家或者单独的艺术事件,例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的奥秘》一书所指向的,是超越作为路径和对象的原始艺术之外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可见,人类学学者们的研究往往基于艺术材料,进而探讨超越艺术的更为宏大的诸如文化相对主义、主客位叙事(emic/etic description)、民族优劣论(ethnocentrism)、象征主义与仪式性以及“他者”的再现政治等问题。在同一时期,如果从艺术学或者艺术实践本位的视角出发,艺术家与人类学研究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如20世纪30年代超现实主义运动与法国人类学(民族学)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关联。立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认为源自毕加索等艺术家在巴黎人类学博物馆所观看的非洲面具和雕塑展览。但是,人类学与艺术实践之间的关联,往往不是艺术史家或者艺术批评家关注的重点。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原因,艺术研究与实践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更为世人所忽略或者刻意回避。
二、 人类学的范式转向与艺术人类学的新发展
由于二战后殖民体系的崩塌以及西方世界内部后殖民反思与民权运动、女性主义等社会思潮兴起带来的社会政治文化批判,艺术界对具有殖民主义倾向和种族主义原罪的人类学始终若即若离。因此,战后西方艺术界在理论与实践中长期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一方面,艺术参与者(创作者、评论家及研究者)试图避免使用人类学方法以摆脱后殖民话语的诟病;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未采用人类学方法接触非西方文化资源而陷入去语境化挪用的境遇而遭到质疑。
从1977年人类学家拉比诺(Paul Rabinow)所著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开始,特别是在1986年由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马库斯所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出版以后,民族志研究者开始对其自身的田野调查实践(动机、理论假设和研究过程与方法等方面)进行强烈而深刻的反思。在反思中,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自身立场及其他主观性因素(如性格、态度和心情等)对于调查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以及对于调查结果的分析和阐释所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他们提出要将调查研究的主观因素进行重新审视。由于研究者们将“主观性”纳入研究实践考量的范围,他们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中便逐渐开始运用诸如“反思性”(reflexive)、“交互性”(interactive)、后现代(postmodern)、“实验性”(experimental)以及“叙述性”(narrative)等新视角对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以及经过重新组织、编辑和阐释的经验材料进行更为全面的观照。高丙中在《写文化》汉译本的代译序中写道:“从1984年的研讨会到1986年《写文化》问世,民族志的主-客体单向关系的科学定位受到强烈的质疑,反思的、多声的、多地点的、主-客体多向关系的民族志具有了实验的正当性。后来的发展说明,《写文化》的出版是民族志进入新的时代的标志。”
在民族志“反思性/实验性转向”的话语背景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类学通过提倡文化多元主义和跨文化对话,逐渐重新确立了其学科的独特意义与当代价值,因此西方当代艺术活动中又重新开始关注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经验成果。这一取向被称为当代艺术的“人类学转向”(anthropological turn/move),又称“民族志转向”(ethnographic turn)。它指的是艺术参与者,特别是当代艺术家在人类学经验传统和反思思潮的影响下,透过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人类学视角,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收集和处理经验材料,以进行艺术作品创作或参与其他艺术实践的当代艺术现象。如今,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文化语境中,这一类艺术活动已不再囿于西方艺术世界,而成为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共同参与的重要艺术景观。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已有传统的知识积累,当代艺术人类学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一) 何谓及何以成为艺术?
艺术并非天然存在之物,艺术的指认和冠名是由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权力关系等种种艺术之外的社会和文化范畴决定的。在许多艺术人类学学者看来,西方的“艺术”概念或许并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或者说,“艺术”在西方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现象,并不见于非西方社会。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关于“艺术”的定义和普遍认识,而且所谓“审美”也并非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而是“地方化”的在地实践和特殊经验(culturally?specific aesthetics)。因此,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认为,在当代,我们应该询问的问题不是“什么是艺术?”而是“一件作品何时而成为艺术?”(When is an object a work of art?)。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为重点的后殖民话语出现之后,有关艺术的定义和反思究竟经历了何种变化?
(二) 风格概念之外的艺术史论述可能
风格(style)是艺术史,特别是西方艺术史中的重要美学概念,它从主题与形式等方面将不同的艺术作品进行归类和区分。然而,这样一种以形式主义为基础的分析方式,正受到强调非西方艺术独特性的艺术研究者、批评家以及艺术家的批判和反思。如此,除了依托原有的风格分析方法外,西方世界内部或者非西方世界是否可以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分析角度和范畴?目前,随着参与艺术(participatory art)与艺术参与实践(socially?engaged art)的日渐兴盛,艺术活动正逐步走出原有艺术史叙述的基本框架,批判甚至否定了康德以来关于审美经验的表述,强调艺术的功能,特别是强调艺术作为一种外部力量介入、影响和整合社会的能力。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在其遗作《艺术与能动性》(Art and Agency)(1998)中即充分表明了艺术人类学在这一方向上所进行的阐述和界定。
(三) 传承人抑或天才
在经典美学理论家,如康德等看来,艺术是极富创造力的人类活动,其创作主体可被视为独立超越、卓尔不群的“天才”。然而,在许多艺术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看来,艺术并非一蹴而就的偶发创作或者完全基于灵感的天才创制,而是基于传统社会的观念、原则和材料而塑造的集体性/匿名性产物,所谓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便是依托传统并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积极且能动的传承人。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艺术创作的个人性和集体性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全球化日益深入和跨文化经验频繁遭遇的语境下,有关个体性和集体性的讨论必定会涉及对异文化的“挪用”(appropriation)问题。这便将有关后殖民语境下文化再现(cultural representation)和再现的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进行了勾连。然而,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等话语表述中,遗产本身的公共性、共享性特质以及在实际的保护过程中的遗产资源化现象,都呈现出一种与后殖民主义不同的经验。这便将问题引向了所谓“全球艺术”(global art)的讨论。
(四) 当代艺术
目前,在当代艺术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领域,“全球艺术”的趋向非常明显。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进入跨文化交流的场域,在当代艺术的展示舞台上进行具有全球化意指的地方性表达。个体艺术家、艺术作品以及相关的艺术运动不再是个人化的操作,而是整个世界(特别是“艺术界”[art world])的合谋与协作。在此,艺术家逐渐转变为艺术策展人或者艺术活动的协调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品制作者。在当代艺术领域,阿恩德·施耐德建树颇丰,是勾连人类学与艺术实践的重要学者。
(五) 艺术田野/艺术民族志
如今,全球艺术的话语促使当代艺术的创作和展示发生了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重要转向,即前述所谓的“人类学转向”或者“民族志转向”。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与艺术学的分析框架和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不断碰撞,后者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前者的研究成果与方法论资源进行艺术实践。以田野调查为核心的民族志方法,逐渐成为当代艺术领域广泛采用的艺术生产方式和理论分析视角。在此基础上,以民族志为基础的艺术形式(ethnography?based art)随之兴起,参与艺术以及协作创制(collaboration)的艺术作品在当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本书《艺术人类学精粹》即是以艺术研究和艺术实践中的民族志方法为主要视角,汇集国外艺术人类学的优秀和前沿成果,探讨不同领域交汇时的方法论可能。
(六) 人类学与艺术新媒介
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艺术创作的媒介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其中最为主要的便是电子艺术或者数字艺术的兴起。在这一过程中,“沉浸式体验”(immersion)和“元宇宙”(metaverse)经验成为获得新媒介艺术审美经验的重要方式,个人的情感和感受成为艺术表达与交流的重要内容和关注点。对此,人类学与民俗学无疑是最为适宜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然而,对于这一方面的探讨才刚刚起步,仍需进一步开拓。
总体而言,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艺术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已经逐渐成熟,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资料收集、理论探讨和分析阐释方法,其中的核心是对于民族志方法在艺术领域的运用和实践。就文献方面而言,艺术人类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其知识生产的积累已较为丰硕。但是,正如《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及《续编》的译者,同时也是“艺术人类学经典译丛”主编的李修建研究员所言,西方艺术人类学的专著数量不多,而且教材类的作品占比颇重,许多成果是以论文集或者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艺术人类学在未来还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深入拓展的空间和理论拓展的可能。
|
|